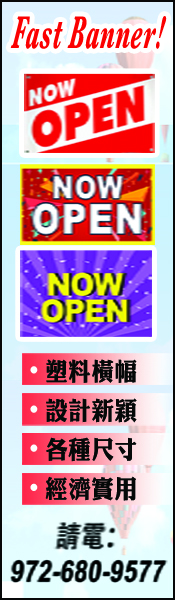【文友社】
|
(續上期)
孩 子
土地下戶後,新成家以五百元,購得了那座水磨房。80年代末,新成家成了這村莊第一個「萬元戶」。
生於1968年的新成的長子福慶,那時正青春少壯。中學畢業的他回鄉務農,晚上磨麵做麵,白天賣麵,福慶成了家裡的主要勞力。新成家妻賢、子孝、老慈。那時除了福慶外,家裡其餘幾個孩子都在鄉上念書。孩子們住校,每週日下午帶上一周的七八斤米,一瓶炒好的鹹菜,每人給一兩元於學校打菜的菜錢。逢著週六娃娃們整整齊齊都回來了,隔壁弟弟家的一脈人也過來吃飯。
那是一生中新成覺得最快樂的時光。
「——咦!全家一大屋子人呢!」新成那日眉開眼笑。
福慶決定出去打工那年,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。三十歲的福慶那年出發,事先沒有徵兆,過完大年,他突然提出,想去達縣打工。
新成沒有攔他。他知道福慶有夢,像村裡所有那一座又一座青瓦院落裡的年輕人一樣,他想走出那一壟一壟的祖屋,出山去看看。
「就帶這麼點衣服?」他問福慶。
福慶頭也沒回就走了。福慶身後,村裡小春的麥苗,已有韭菜高。
村上開了一紙介紹信,就帶了五六百元車錢,福慶上路了。福慶先去了萬源,後來去了達縣,再後來去了越來越遙遠的南方深圳。
福慶一走十四五年,如今深圳已成了福慶真正意義上的故鄉。福慶全家安家深圳,大女已嫁作人婦,二子大學畢業,在北京一家建築公司工作。福慶的三女兒,學化工,今年剛考上重慶一所大學。
跟著福慶去外面看世界,新成的其餘幾個孩子中除了二女嫁了鄰鄉人,一個兒子,兩個女兒,都在不同的城市做工。
幾年前,孝順的福慶接新成夫婦去深圳玩,後來,在北京做包工頭的小兒子,又請他二老去北京開眼界。城裡的熱鬧、繁華,鄉里自然是比不了,但城裡樣樣都得花錢,這讓二老不甚習慣。儘管兩個孩子都盛情挽留,但他們執意要回家。在家裡,地裡隨意采一把青菜,挖一鋤紅苕就可以過日子。最重要的,白日裡,孩子們上班上學去了,忙了一世的二老,無所事事,惘若廢人。
再回到龍王橋時,新成發現,他弟弟家的一脈人正商議在縣城購房的事。新成弟弟家的幾個娃也悉數去了城裡打工。不久之後,新成弟弟全家,連同子子孫孫,全搬去了達縣和萬源城裡。至此,曾經有著近三十口人住在這裡的家,這個熱鬧了上千年的舞臺上,一束追光中,只剩下,孤零零的新成與他的結髮老妻。
已記不得是哪一年,萬源市羅文鎮經廟埡鄉到鷹背鄉的公路通車了,新成家的門前,行人漸少。
2000年之後,這段公路上全線跑起了私營汽車,新成家的門前,這條曾經的古道,再無人跡,除了這一對背微駝的老人,以及孩子娘用蒼老的手指給我看,那牆上佈滿塵埃的一個舊相框裡,她曾一把攬在懷裡的那幾個小娃。
永 懷
「……知柏樹兒知柏尖,陽雀笆(築)窩笆(築)中間,哪個撿到陽雀蛋,十個兒子九個官。」
「一聲喲呵號,(眾)喲兒喲呵嘿。二聲喲呵號,(眾)勁展一。三聲喲呵號,(眾)齊冒力……」
「大山翻過梁山伯,小山翻過祝英台……朝中要數哪個強,文官要數包文正,武官要數楊六郎……」
另一叢空蕩蕩的院落,這村莊年歲最長的知客師唱耕田、打夯、拉石頭築路上坎的山歌給我聽。「山歌本是亂劈柴,哪裡想起哪裡來。」厚厚的棉衣棉帽裡,老知客師張達信老人,像個嘰嘰咕咕快樂呢喃的嬰兒。但他一旦入角兒,那聲音仿佛自天外而來,異常亮堂。
達信老人家的後生們也都差不多進城做工去了,於「門」字形大院的青石板院壩,他的三歲的小孫女依在他懷裡,仰著頭看他唱歌。
村支書永懷的家,就在達信家不遠的山坡下。1962年出生的永懷,他的三個成年的孩子,也都進城務工去了。
那個午後,他埋頭往他家的火龍坑裡不住地添柴。在村小念書的一對小孫頭搖搖晃晃背著書包從光亮處走進屋來。
正念小一和小二的兩個孫頭就讀的是本村的村小,村小共有二十幾個娃。當年永懷也於此念書,他上一輩人新成老人兒時也在此發蒙。
寺廟不大。新成念書時,佛堂外,一位善知識捐建了規模龐大的一座過殿,過殿裡一尊觀音聖像。四周無數的小菩薩。下課時,娃娃們就在菩薩像間穿來跑去。過殿毀於破「四舊」。永懷念書時,這裡只剩下原來那間老佛堂了。老佛堂張舉人那個時代便有了,如今更名義莊寺。
義莊寺佛堂不足五十平方米,須彌座的蓮臺上,三尊佛菩薩。空空的堂前,永懷記得,當年自己念書時,幾個年級的學生分年級坐在一起。同一個老師分時段,給不同年級的學生上課。
如今的村小依舊於此,不同的是,寺廟只是學校一景,這座古老山村的鎮村之寶。學生坐進了寺廟一旁蓋起的兩間教室裡。
寺廟的後面,不遠處的村北,是舉人張玉恩的「山」(墓)。那日去朝「山」,一棵幾人才能環抱的銀杏樹,樹前是舉人壯觀的墓群,樹後是舉人的後人所居住的祖屋。倒「凹」形的院落,瓦簷下曬滿玉米,一隅的風車上棲著雞子。一條狗遠遠地吠。凹字最中間,那間鄉人祭祀拜高堂用的堂屋屋簷,檁上瓦片稀疏,堂屋裡恍若天井,一叢竹子,從屋內高高地穿出屋頂。
許久,有人從拐角處的一間屋裡走出。
他是舉人的第六世後人。住了整整六輩人,老人張德金說,他的所有親人,他的兄弟姐妹們以及他們的孩子們,都走了。自己的三個兒子也去了遠方,一個在海南,一個在深圳,一個在太原。孝順的娃們走出了大山,先後帶走了生養他們的長輩。
老人纖纖弱弱地笑。他的身後,出走人家的一組組聯繫電話,這些城裡與鄉間最脆弱的最後一線依戀,幾扇緊閉的木門上,歪歪扭扭地寫了一門。 …………
在這座有著一百一十多畝土地,面積約五平方公里的田陌間,星星點點地憩滿這樣的寂寞院落。這是村支書一頭濃發早早白去的原因。
那晚去村主任家吃飯,摩托車停在遠遠的村公路口,我們沿著一條雜草叢生的鄉間山徑前行,不幾步路,天就黑盡。徑旁,偶然一星亮,或是一盞燈。永懷歎,「這院……也只剩兩位老人……」
一千四百多人的一個古老村莊,留下兩百多號老人及兩百多名兒童,有的生產隊年輕人幾乎盡數出走。全村最年輕的勞動力在五十歲以上,這樣的「老年農業」該如何生存與發展,夜裡,他常常猛地驚醒,再無睡意。
有明月的清晨,那一門電話號碼,謎一樣安靜
那夜在村主任家,村支書,村主任,還有村小的校長,村裡的三個「年輕人」一邊吃一邊算一筆賬。年前他們自費去外地考察,今年村裡種了一種韓國辣椒,這裡的土地富含對人體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「硒」,他們厲兵秣馬,準備以健康食品「萬源紅」去突圍。
一畝辣椒,是過去種小麥收成的四倍,全村共七個村民小組,哪一組種植多少,收成幾何,他們很平素地聊天,我卻於心底不敢有絲毫懈怠地默默記下。頭一天,村小王校長的話,我也記下了,記在心底的另一頁:
村小目前尚需:
籃球兩個
教學用的米尺和積木各一
教學用的正方體、長方體、圓柱體模型各一
還有一項,因費用較高,他們一時未敢設想:村小升旗用的旗台和旗杆。材料加上人工費用約需兩萬元。這是必須要有的,因它所開啟的,是人的敬畏之心。無論于國家,於尊長,還是于天地于鬼神於萬物,有敬畏心,人方有風骨,一個時代方有可以繁衍延續的精神根基。從前村小的旗杆是有的,樹木做的,後來因建教室被拆。村上期待能建一個像樣一點的旗台。 …………
年輕人都在城裡做工,這裡其實不缺乏城裡人才擁有的消費特權。每一家幾乎都有一種可以一邊取暖一邊煮菜的火鍋電桌子。此外,各式城裡流行的實用小家電,在外的遊子們總是第一時間買好後速寄回家。手機更是普及到了每一戶,甚至每一位留守於故鄉的老父老母,各一部。
山那邊的新成老人來電催促我回家,坐在永懷支書的身後,漆黑中,看不見四下裡,剛播下的小春作物小麥的麥苗。摩托車於山路上顛簸,我想像,它是麥苗正一點點在破土。
第三日,農曆二十三
早 酒
傳說當年外鄉的匠人給那牌坊戴帽,始終不順,後來匠人悄悄詢問新成姑祖母的母親,此前老夫人可有言行不妥處?老夫人直搖頭。想想將正納鞋底的針往頭上一劃,又細聲道:倒是有一回,一對雞子正行那個(交配),我沖著它們笑了一下。
這一講,帽子戴上去了。
古老的村落不乏古老的溫情與文明,也不乏古道熱腸。
整個山村沒有餐館,連日來,我在新成老人、村支書、村主任,還有新成老人所在那個村小組的組長家,輪番用餐。吃「轉轉飯」。這裡人有吃早酒的習俗,一大早也會弄幾個菜喝上一口。村主任飯桌上講笑話,你要是不走,住上半個月,我用廣播通知到戶,天天會有人請你到他家吃飯。保證每天不重複。他們指不定會多高興。
這一季,因為家家戶戶的勞動力不夠,永懷支書所在的義莊寺村民組,今冬小春作物只種了十來畝。這是一個人口相對集中的大組,從前該組會種七八十畝。全村共七個組,目前有四個組的年輕人悉數進了城,那幾個組的種植情況,不得而知。
吃過早酒離開新成老人家的上午,新成的老妻——日日盼著孩子們能早一天回家的孩子娘,怕著涼沒能出門,新成老人站在舞臺的前端一直揮手。我遠遠回頭,特別怕,一落手,作別的,不僅是可能再也見不到的已是食道癌晚期的老婦、最後的古驛站人家,還有,是於現代化進程中正漸漸淡遠的纖塵不染的鄉村,那個雞犬相聞、春田漠漠、可行馬遲遲歸的舊夢。
古老的鄉村,這路,到底該怎樣走……
「二十一二三,月起雞叫喚」,這是這個古老村莊念了千百年的諺語。
後來知道,我所在那裡的幾日,正趕上這日子。
農曆的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,每月此時,被稱為「中國南北氣候分界線」的這大山深處,夜別樣濃稠,伸手不見五指。不管白日裡世界多麼喧嘩,那些夜,朗月只在雞鳴之後才悄然下床,為天空,掌一盞孤燈。
有明月的清晨,那一門電話號碼,謎一樣安靜。 摘自熊鶯《遠山》
回上一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