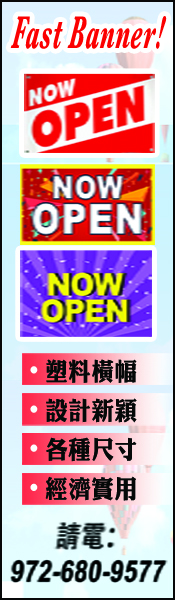【文友社】
|
A
我從廁所裡走出來,一眼就看見主任K從走廊那頭走過來,我嚇一跳,趕緊溜進辦公室,在桌子邊端端正正坐下,眼睛盯著電腦螢幕。心裡數著數,1、2、3、4……就聽見咚咚咚的腳步聲,等我數到12的時候,K出現了,他停住了,目光似劍一般掃進屋來,我趕緊埋下頭。我們辦公室的門是不能關的,因為屋內兩個人是大樓裡最低一級的辦事員,所以必須時時敞開門,接受審視的目光。有一次同屋的小王關了門,被K訓得腦袋像雞啄米。
待我數到28,偷偷地抬起目光,我的判斷一點都不錯,K已經目巡結束,正要轉過他向日葵花盤一樣的大臉,處於將轉未轉之時,所以我把他的表情窺視得一清二楚。啊,K的眉心緊緊擰在一起,兩顆眼珠凸起,像是甲狀腺亢進的病人,大臉變陰,好似要刮起一場風暴。難道我們做錯什麼事了?正在我心怦怦亂跳的時候,他神色忽然變了,好像想明白一件事,眼珠返回原處,臉上的肌肉鬆馳下來,露出一種神秘的微笑。
我明白了,阿彌陀佛,他的情緒和我無關。K往前走了,咚咚的腳步,不出七步,打開他辦公室的門,滯留十秒鐘,呯地關上。
我長舒一口氣,抬眼看對面的小王,他額上的汗都淌下來了。這樣看來,他比我還要不經世面。現在,我悄悄地掏出珍珠奶茶,安閒地喝一口,趁神經鬆馳時,介紹一下自己。
1988年夏天,我出生在一座離海不遠的三線城市。我的爸爸懦弱無能,在一個工廠裡管倉庫。媽媽年輕時非常漂亮,在老爸面前說一不二。我初中一年級的時候,有個高中學生對我說,她是出了醜之後才下嫁給武大郎的潘金蓮。我當時臉都氣黑了,卻按捺不動,吃午飯後我藏了一根棍子,暗中跟上去,敲破了他的腦袋。校長對我拍桌子摔凳子,說我破壞了學校的年終評比,發誓要扭送我進公安局。結果他沒有找來員警,卻找來我的媽媽。我媽漂亮的臉擰成了苦瓜,她當著校長室裡的6個人,當場給了我兩記響亮的耳光,讓我眼前飛起一群嗡嗡叫的黃蜂。我氣得渾身打顫,我是為你啊,你卻讓我蒙受奇恥大辱!
沒想到出了學校,她卻帶我上肯特基,雞翅、漢堡點了一大堆,平時不准我吃的聖誕,都點了紅白兩個。我吃得連連打嗝。走出店的時候,她對我狐猸地一笑,刹那間,活像一隻狐狸。我頓生疑惑,是不是我不應該敲那人的腦瓜?
我整個求學期,都沒有什麼好誇耀的,就像一本稀鬆的沒有亮點的破書。可是畢業了,我北漂的經歷卻充滿了驚濤駭浪,盡是辛酸的眼淚和苦悶的孤獨。我的媽都明白,她在手機中對我說:我的兒,回來吧!北京有什麼好?不對,北京再好都不是我們的!我們沒有根基,一根在水中漂的野草,連紮根的泥土都沒有。兒啊,回來吧,回到媽的身邊,縣城雖然小,可這是我們的家。
我帶著哭腔對她說,回來能幹什麼?縣(市)裡像點樣的工作都輪不到我,讀再多的書也沒有用,都給皇親國戚把持了。
我的媽也歎氣,歎完了用堅定的聲音說:不要沮喪,有你媽呢。
我的媽果然是個女中豪傑,到底還有多少人依然認她那張染了風霜、依舊漂亮的臉,我一概不知道;她踏破哪些門檻,耍了哪些女人家的手段,我也不知道,我唯一知道的是,我終於走進考場,還有人專門打了招呼。這樣,我謀到了一個美差,一星期上五天班,每天坐八小時。我心裡明白,只要在這張椅子上坐穩兩年,不出事,我就能進入了榮耀的編制隊伍,隨後在這張椅子上終身到老,這就是市里許多年輕人的理想。可我卻不知道是應該興奮,還是失望?
我已經枯坐兩個半小時了,可以跑出來放鬆,我好像一隻從籠中出來的小鳥,輕快地飛到院子中。院子不大,也就百來平方米,東頭種了一棵銀杏樹,西頭也種一棵銀杏,都要三人合抱,樹葉茂密,結了許多銀杏果。我走到東頭銀杏,繞它一圈,再走到西頭,也繞西銀杏一圈,這樣來回五趟,心裡有些舒暢。我知道,這也是我事業的一部分,我要作長期的思想準備。
我走到東頭,看見窗子開著,往裡一看,卻看見了主任K。看他神色似乎在做一件莊重的事情,他全神貫注,大臉上沒有一絲放鬆,他手上拿著一枝紫色杆子的長鋒大筆,面前放著一個畫架,架子上有一張2A的白紙,他在紙上畫圖。畫的是什麼,是一頭羊,一頭公羊,臉上有可憐兮兮的神情,仿佛它已經看見了屠刀,所以很悲哀,我不客氣地說,它臉上似乎有人的神情。
我心中大驚,呼吸急促起來。K怎麼會在辦公室裡畫羊,他畫一頭公羊幹什麼?他今天上班時神情不好,後來又驟然變好,難道都和這頭羊有關?就這時,K站起身,向窗口走來,我慌忙往後退,躲到東銀杏的樹幹後。他走到窗前,伸出頭,向兩側望瞭望,我斷定K沒有發現我,隨後他退回去,坐到椅子上,從內衣掏出一顆丸子,有玻璃彈子那麼大小,咖啡色的,放進嘴裡。
我心怦怦亂跳,不知道是為什麼,“我不過是看見他畫畫,沒有大不了的。”我試圖說服自己,可是不行,我還是驚慌。好好的在辦公室裡,畫一頭悲哀的公羊幹什麼?還吞食一顆咖啡色的藥丸,這有什麼作用?很可能我看見了不應該看的情景。
B
這天上午,我校對了一份稿子,打了兩份材料,半天算對付過去了。我走出樓,想上食堂,忽然有人叫我,我轉身看,是楊樂明。楊樂明五十多歲,臉顯狹長,穿件米色的衣服,站在陽光下燦燦發亮。他是我老爸所在工廠的總經理,聽老爸說,他待員工不錯,一次老爸不小心,腿骨折了。他在醫院裡忐忑不安,因為是他沒有遵守勞動規則,違規操作造成的。但是,楊總叫他的助手到醫院來看望,送來了營養品,叮囑老爸好好養傷,不用擔心倉庫的事,工資獎金照發。把老爸感動得老淚縱橫,到哪裡都說楊總好。
“你就在這裡上班?”
“是的呀。”
他笑著說:“不錯,你替老金掙臉了。”
他說的老金就是我老爸。我心裡說,您說得不對,是我媽替老金掙臉了。
“楊總,您來有事嗎?”
“要是沒有事,我就不上衙門來了。”楊樂明忽然情緒變得不好,“不管什麼大官,總要講道理的吧。”
“您是找主任K?有難事了?”話剛出口我就知道不對了,我問的太多了,我哪有這個資格?
“難啊,還讓不讓企業活了?不說了!”楊樂明跺一下腳,狹長的臉上蒙上一種悲哀、無奈的神情。
我突然驚住了,他的神情我好像剛見過,像什麼?此刻他背對著我,我移一下腳步,他也移一下,陽光照在他臉上,我想起來了,此刻他像一種畜牲,像K畫的那頭公羊!我剛才說了,羊狹長的臉上有種人的神情,就像楊總現在的神情啊!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真是人間怪事,一般的羊不可能有人的神情,K筆下的公羊怎麼會有呢,而且恰恰發生在楊樂明來找他的時候。
我腦袋發暈,我發現什麼了,是一件可怕的無法言說的秘密,還是我神經錯亂、胡思亂想?
“你怎麼了,不舒服嗎?”楊總一雙窄長的眼睛盯住我的臉。
“沒有,沒有。”我勉強穩住,聽到一聲雄壯的聲音,我回頭看,K出現了,從長長的半明半滅的走廊上走過來。“我走了,去食堂吃飯了。”沒等楊總回答,我慌慌張張逃走了。跑出一段路,我回頭看,K的手和楊總握在一起。
我今天食欲不好,沒有吃幾口,就從食堂裡走出來。忽然想起,不要遇上楊樂明,這會使我十分尷尬。還好,走廊裡空蕩蕩,沒有一個人。咚一聲門響,K出現了,從他的辦公室裡走出來。我大吃一驚,我看見了什麼啊!
K大臉上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,仿佛他剛從一場很費力氣的搏鬥中勝出,神情果斷、堅毅,又帶著不掩飾的欣慰。他手上有根繩子,牽著一頭公羊,再細看,這頭公羊不就是A2紙上的麼,它怎麼從紙上跑下來,被他牽著在地下走了呢?
“小金,你怎麼不去吃飯呢?”他明顯對我這個時候出現很不滿意。
“我,我剛從食堂出來,我已經吃過了。”
羊突然叫了一聲,我低頭看,差點昏厥,它哪是一頭羊,它眼睛裡流露出的分明就是楊總的神情,難道它是楊樂明變的?
“你是不是對這頭公羊很好奇?辦公室裡出現一頭羊,你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?”K的眼睛像匕首一樣逼住我。
“沒有,沒有,辦公室裡有是可以出現一頭羊的,如果有人買了一頭羊,一時沒有地方放,很可能寄放在您的辦公室裡。”我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。
“嗯。”他大臉上的神情有點放鬆,“明白就好,小金,我沒有看錯,你不是一個糊塗人。”
這時,門口走進一人,身子魁梧。K欣然地叫起來:“你來了!我正等著你呢。”又轉臉對我說,“說曹操,曹操到。羊的主人來了!”
那人用粗壯的嗓子回了一聲,大步走過來,用專業的眼光看K手上牽的羊,打個飽嗝,“不錯,這頭羊不錯,能出40斤肉!”
我心裡疑惑了,K說羊是他的,他怎麼像剛看見一樣?我再細看,不對,這人臉上有橫肉,就是菜市場裡的王屠夫!我多次見過他,腆著個肚子,兩隻大手血淋淋的,伸進羊熱氣騰騰的肚子裡掏。
K把繩子往王屠夫手裡一塞,“ 滿意就行!牽走。”王屠夫就來拉繩子,那頭羊似乎什麼都明白,就是往我身子後躲。我看它,眼裡都是悲哀和懇求,我心一酸,眼淚要掉下來了。但我又能怎麼樣呢,我能把它抱住,不讓牽走嗎?
我身子一閃,躲過去了,可是公羊繞著我兜圈子,好像我是它唯一的救星,還張嘴咬住我的褲腿。王屠夫來火了,罵道,“你是羊,就是這個命!”他一手掐住羊的頸子,一手扯住它耳朵,兩邊一起使力,羊就嘭地倒下了。他牽了就走,羊“妹妹”苦叫著,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他忽然吹起了口哨,得意的哨聲在走廊裡回蕩。
我呆呆地看著他們消失,回過頭,K一雙眼睛像黃蜂一樣盯在我臉上,“你好像很有看法?”
我慌了,“我哪有看法,我一點看法都沒有。”
第二天,我們全家在一起吃晚飯,我沒有女朋友,除了偶爾和朋友在外吃燒烤、涮火鍋之外,都在家裡吃飯。老爸端著小酒盅,喝他的二兩高溝,我和媽媽直接吃飯。
小酒一下,老爸的臉紅了,臉上浮起愁雲,“真是怪事,楊總忽然不見了,晚上十點不回家,楊太太以為在公司裡,打電話是嘟嘟嘟盲音,找到公司,早就黑燈了,人影都沒有。找他的朋友,說中午就和他聯繫不上了,所有的朋友都是搖頭……慌忙報警,到處都找了,十多條船打著燈,河裡篩了幾遍,影子都沒有。”
我心裡一驚,看來我昨天所見的不是幻影,那頭公羊真是楊樂明所變,說不定已經讓王屠夫開膛剖腹了。但是我能說嗎,說出來又有誰會相信?不要說聰慧絕頂的老媽會認為我中了邪,就是老實巴結的老爸也不可能相信。再說,我說是大主任K把楊總變成公羊的,那證據呢?我手上沒有一點證據,那就是誣陷,K能饒過我嗎?他能把楊總畫成羊,當然也能把我畫成別的,臭蟲、老鼠都有可能啊。
“好人怎麼都沒有好結果?”老爸的眼睛紅了,目光轉向我。我忙把一個鹵蛋囫圇塞進嘴裡,好讓自己不發聲。
“這是你急的嗎?”老媽兩條柳葉眉挑起來,“你一個倉庫保管員管得了總經理的事?你把自己當誰啦,跳上秤盤上去稱一稱!他一個總經理,三頭六肩,四通八達,什麼可能沒有?要是他集資斂財,捅了大窟窿,卷款跑掉,難道會提前通知你?要是他在外面養小三,生兒子,早就留了路,現在逃進極樂世界,也會告訴你?”
“這,這……楊總不是這樣的人吧?”
“人家一點小恩惠,讓你念叨一輩子,也就你是個傻瓜。這年頭,什麼樣的人沒有,什麼樣的事不會發生?”老媽臉上透出世事洞明的光亮。
第三天,老爸回家,坐下就說:“這楊總還真是花花腸子,他帶著情婦、私生子溜了,有人在上海浦東機場看見他哩。他戴著大口罩,戴著一副墨鏡,可還是有人認出了他。月娥啊,你的眼光真厲害。”
老媽不答話,只是冷笑,從牙縫裡透出風。從此後,老爸再也不提楊樂明了,楊總派助手來醫院看望他的事,也被老爸拋入爪哇國了。
原來世上的事都是這樣的,個中的原委曲折有誰知道?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悲哀。不過,這悲哀只能我獨自享受。
回上一頁